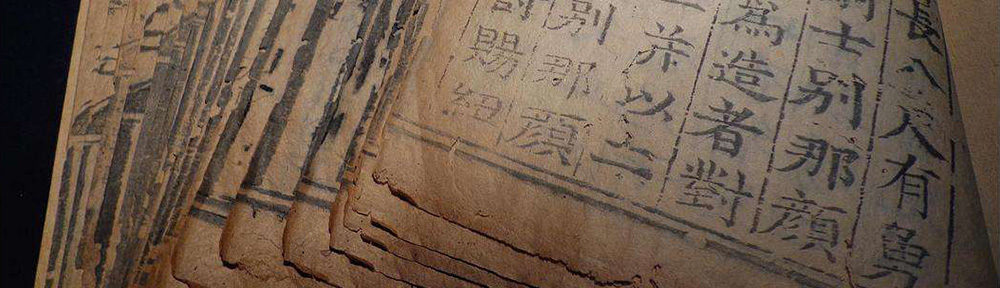除了西藏、新疆、黑龍江三省里部分極偏僻、習俗懸殊的少數民族地區,在斷定時辰時需求考慮時差外,全國大部地區大約可用北京時刻來劃定時辰。
每天要區分12個時辰,是因為陰陽五行的特征及旺衰會隨時點的改變而改變。首先要理解,推八字的干支理論不只是是描繪自然規律的,它更是個人類社會文明的產品,從誕生那天起便是為人類服務的,一起描繪社會的一些客觀規律。所以把太陽日照的狀況作為陰陽五行的特征及旺衰改變的僅有標桿,我個人認為不符合原詣。原本嘛,陽和陰就不只是對應太陽和地球,一起它們還可以對應單和雙、公和母……等等。五行就更雜亂了,地支更是陰陽五行的組合體,老實說它們跟日照的聯絡不行緊密。陰陽五行的特征及旺衰的改變應該是由多種自然環境要素、多種社會環境要素一起效果的成果,它有個客觀特質是——與時“變易性”。
咱們現在的社會結構、信息結構及各種相關要素,跟古代有極大的差異。
古人傳遞詳細的圖文信息,最快的只能用飛鴿傳書。假如信鴿滿足走運的防止成為下酒菜,它把信息傳到千里之外恐怕也要一天時刻。這個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,只是在軍事上運用較多,所以對社會整體的信息相關效果微乎其微。一個人出外經商,納了妾生了兒,家里的原配壓根兒不知道摔醋缸。乃至還常產生“挑花源”事情——不知有漢、不管魏晉。這時候,地域(對應時差)的遠近對社會結構、信息相關性的影響適當的大,考慮用真太陽時很有必要。
現在的社會信息相關性太強、太敏捷了。在北京生了胖小子,打電話給西安的老爺子報喜,也便是一會兒的事。上證指數一跌,遍布全國的億萬顆心臟在同一秒內收緊。當今的信息時代可謂“全球同此涼熱”。
所以,我國的大部地區同在一個相關性很強的信息圈內,社會結構的緊密度是那么的高,具有很強的一起性與共振性,簡直可疏忽地域、時差的影響。有個概念叫“地球村”,引申到我國也便是個“小村屯”,一個小村屯當然是不需求考慮地域時差的了。
當然,我得出這樣的定論不單單依托以上理由的支撐,一起還有我個人及其他一些易學研討者的實踐經驗。盡管還沒有更科學更緊密的證明進程,也沒有更準確的定論。但我的意圖是拋磚引玉,期望更多的人參加易學的研討,研討它的與時變易性。
祖父筆記文章,轉載請聯絡!
隨機文章: